最近有一部電影《流麻溝十五號》上映,講述著在白色恐怖年代,一群女性受刑人的故事。根據電影的描述,多數的女性並沒有什麼讓當時政府該感到擔心的言論或行為,但是她們就是被認為是對政府有威脅的,所以被關到綠島。在那個年代,雖然我們理論上應該是個自由民主的國家,實際上卻是集權統治,上級的一個命令,就可以決定一個人的生死。
面對這樣的制度霸權,有些人選擇順從,有些人選擇不配合,有些人已經身心交瘁到任人宰割。在看電影的過程中,讓人非常難受,因為那些都是很年輕的生命,卻被主事者當作是敵人一樣在對待,真是太沒有道理了。
在電影中,那些不配合的人,都沒有好的下場。其他的人雖然活了下來,但我想她們心中應該是百感交集的。因為她們可能會想,如果當時我也站出來反抗了,那麼結局會不會不太一樣。但依據電影的描繪,以及對於那個年代的想像,我覺得應該是很難有不同的結果。當然這可能是因為我自己略悲觀,但在那個資訊不流通的年代,要串聯群眾的力量,是不容易的。
制度霸權從來沒有離開過
雖然現在我們身處的環境,感覺起來是相當自由民主的。但是,制度的霸權一直都還是存在著,只是我們可能習慣了,或是沒有察覺到這件事情。比方說,很多時候,我們在講離開一個單位的人,如果回來看看在舊單位的夥伴,我們可能會用「回娘家」來形容這樣的行為。我也是經人提醒之後,才驚覺,這個說法很像有點壓迫女性。
諸如此類的事情,實在非常的多。前幾天我聽了政大社工所所長王增勇的演講,他舉了一個例子,讓我印象非常深刻。他介紹了家暴受害者要申請保護令的過程,就是一個制度霸權的展現。他說一位受害者要能申請到保護令,這位受害者最好是要有驗傷的紀錄,也就是說這個制度認為你要在肢體上被凌虐了,才算是被家暴。如果沒有驗傷紀錄,那麼至少要對這個過程有清晰的記憶,否則就不會被判定需要保護令。但是,實際的狀況是,不少家暴受害者已經有創傷經驗,對於當時發生的事情,有可能有失憶的狀況。所以,我們又再次看到制度的霸權。
通常當我們是既得利益者的時候,我們很難察覺到制度霸權的存在。比方說,對於一些性別認同和自己生理性別是不同的人,在填寫任何需要表明自己性別的資料時,就會覺得自己被制度霸凌了。這樣的感受,我想就不是多數人會有的,而你之所以沒有這樣的感受,就是因為你的權益並沒有受到損害,你被制度保護了。
很多制度本身,都很不合理。像是前一陣子大法官判定政府不讓西拉雅人登記為原住民「違憲」,就突顯原住民相關的制度是有問題的。到底什麼樣的標準,才算是原住民,老實說這沒有一個絕對正確的答案,都要看制度是怎麼定義的,以及是否有被徹底貫徹。以西拉雅族的例子為例,就跟制度沒有被徹底貫徹是有關係的,所以原民會必須要進行修法。只是,修法之後,會不會導致西拉雅族就不被認定是原住民,這也是有可能的。
對制度霸權不敏感,比較好嗎?
這個問題很難回答,如果你一直都是比較順從的人,不喜歡去挑戰制度,你的日子似乎也過得去。因為你會找出一個規則,幫助你可以在現有的制度下安身立命。就如同在兩性極度不平權的年代,多數的女性似乎也活下來,也沒有特別數據顯示他們的幸福感,平權年代的女性低。
就像在現行高等教育體制下的老師們,若乖乖照規定來做研究、發表論文,他日子也是過的去的。如果你沒有照制度來做事情,你反而會比較辛苦。雖然這樣的制度看起來有因為大家的意見而做出調整,但調整的速度實在太慢了,對於不願意屈服於制度的老師來說,是相當不利的。
對一般企業的員工來說也是一樣的,公司有自己制定的KPI,可能對你非常不利。如果你選擇不要追求公司的KPI,那最終倒楣的人,不是別人,是你。所以,很像乖乖的,會讓你過得比較好。因為當個反制度的人,不僅會被別人標籤化,也不一定能夠造成制度的改變。
我在聽王增勇所長演講之後就問他,那如果我們發現制度不好,建立了一個新的制度,但很有可能就是另一個坑,那怎麼辦?王增勇所長說,那就看你是要當一頭快樂的豬,還是痛苦的人。我問了幾位周邊的朋友,他們說當然是當快樂的豬啊~

我自己還沒有想清楚,但我知道對這些不平對待敏感的人,一般來說真的都比較痛苦,因為他們太容易感知到不平等,因而會有負面的感受。我感謝有這樣的人,讓制度制定者不會恣意為所欲為,因為他們知道有人在監督著他們。
不滿制度霸權,不代表就要反對制度的存在
當然也不是說只要有制度的地方,我們就要認定有所制度霸權的現象。這就要取決於制度是怎麼在團體中運作的,如果制度是可以依據群體中成員而做彈性修改的,並且盡可能滿足所有人的需求,那麼有制度就不一定是一件壞事情。畢竟,當一個地方都沒有制度的時候,做事情就不是那麼方便、有效率。
像是在哥本哈根有個地方叫自由城,這個地方基本上是一個自治的區域,政府部門也拿他們沒辦法。若在這地方要做出什麼改變,難度是非常的高,因為每個成員都不覺得,別人有權力可以來指使他要做什麼。只有當他們想要做某件事情的時候,他們才會做這樣的事情。

因為我有機會跟幾位丹麥人聊天,從他們的觀感中,他們對這群人是尊重,但不必然就是認同的。也就是說,這個自治區對他們來說,是一個特別的存在。但至於是否象徵著他們社會是比較進步的,那就不一定了。
有時候我會想,我們的制度之所以會看起來很專制、不民主,可能都是因為一些搞小聰明的人所造成的。因為在我們的社會中,有些人用了不好的方式,來幫自己獲得一些好處,以至於規定越來越嚴格。幾周前,我在高鐵上,就遇到車長查到兩位乘客,沒有帶學生證確買了學生票。雖然他們有可能是忘記帶學生證,但我認為他們更有可能是借別人的身分買學生票。類似這樣的例子很多,以至於我們的制度就會越變越嚴格,也間接提升了制度的霸權。
那我們可以怎麼辦?
第一種作法比較龜縮,有點像是當一頭快樂的豬的作法,只是你並非無視於制度霸權的存在,而是可以用另外的角度來看待這件事情。制度本身既然規範了你的作為,那麼也就必須要為你的作為負責;你若這樣想,反而會覺得自己減少需要承擔的責任,感覺也還蠻不錯的。
像是日前郝明義在國家兩廳院輪椅卡住了,尋求工作人員的協助,工作人員表示他們不能協助,因為是違反規定的。旁觀者會覺得這制度荒謬,但之所以會這樣,應該是工作人員曾經協助,結果反而惹禍上身。於是,乾脆禁止他們去協助觀眾。若從工作人員的觀點,雖然他被限制了,但他某種程度上也是被保護了。
第二種作法就是制定自己的制度,建立自己的價值體系。這樣的作法,不一定就會衝撞社會體制,而是可以在制度的灰色地帶找到生存的空間。就像自學制度,一開始也是走在灰色地帶,直到規模越來越大,政府才不得不正視這樣的作法,並且訂立相關的制度。
你不一定要走上被主流認可的地步,但是若你希望別人可以尊重你的制度,那麼你不該影響其他人,這樣制度比較有可能被保留下來。
第三種作法是最不容易的,就是去衝撞制度,讓制度可以發生改變。像是各種罷工,就是很好的例子。只不過在亞洲地區,罷工的成效通常有限,因為我們過度強調社會的和諧,而不重視自身的利益。
年輕的我,可能比較會採取第三種作法,會去衝撞制度。但我後來發現,略帶妥協的衝撞,往往效果會比起直接衝撞來的好。我自己也會跟學生說,你今天要抗議制度不好,沒有問題,但是你要提出一個更好的制度,不能只說現在的制度不好。要挑別人的毛病很容易,但是自己要端出一個別人挑不出毛病的東西,沒有想像中的簡單。
所以,好好檢視現有制度的問題,想辦法從中去找到可能的調整方案,是我覺得比較好的做法。當然,這一切的前提是,有權力的人,必須要有足夠的雅量,願意去調整制度,以及自己對於制度的看法。從歷史上也驗證了,那些可以聽進去建言的君主,往往能創太平盛世;那些獨裁的人,通常下場不太好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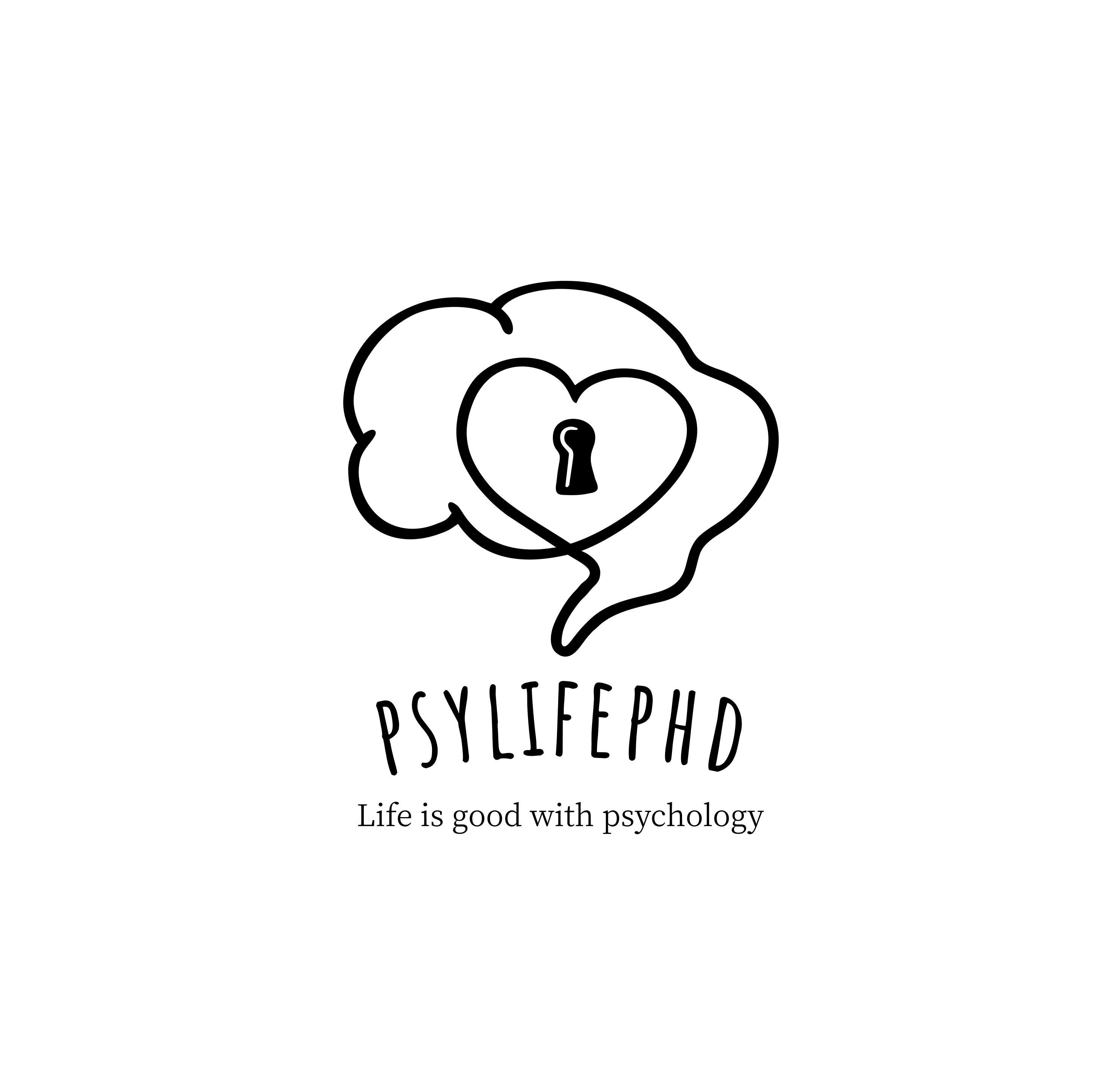

發表留言